 我的爷爷–爷爷劳动之编萝头原创
我的爷爷–爷爷劳动之编萝头原创
当爷爷去世的时候,附近好几个村子的人都提到,闫店岗编萝头那个老汉儿,没有了…
一个人一辈子会有无数的标签傍身,有些是自己掌控的,有些是别人附加的,有时候标签会显得很片面,无法概括一个人,但是有时候标签又是十分凸显的,正如上边那句话里边一样的,爷爷给到外村人的最大一个印象,就是:编萝头的那个老汉儿。
这里所提到的罗头,是农村非常常用的一种农具,几乎家家必备,而且因为干活的时候用扁担挑会更加省力,所以每家都最低有两只,按说会有非常好的市场,加之附近几个村庄并没有别的人会这个手艺,按说爷爷每年编出来的,应该能够非常抢手,但是由于爷爷所编的都过于结实,一般一对罗头买回家之后,用上四五年,只要不是有虫子蛀了,那么基本上是不会坏的,所以并不见得市场多么紧俏,但这些都不重要,编萝头是爷爷每年的一件大事儿,他从来不去管顾后续市场的问题,而只是用心做好每一个步骤的事情,年复一年,这样的工作,直到临终的前一年,在家人的竭力制止下,他才终于放下不做。

关于爷爷与编萝头的事情,应该有很多很多很多,无奈的是无知道的却太少太少太少,而今想起这些问题,却已然不能够再当面朝爷爷讨问,不免得悲从中来。三月,我从公司请了陪产假回到老家,昨天吃过晚饭陪媳妇散步,走到东边之后,我便提说,咱俩去看看咱爷吧,她当即应许,于是我搀扶着她,踏过脚下虚虚的土地,携手来到爷爷的坟前,给她讲讲爷爷奶奶终于能够相逢了,而后便携手而归,纵然新坟在目,仍旧不能够相信我那可亲可爱可敬的爷爷,竟然已经不在二月多了。写至此,禁不住眼泪打转…
# 1,暮年学艺。
事实上编萝头的手艺,是爷爷在六七十岁左右的时候,认真与人学习之后才掌握的技艺,模糊记得他说过当时学艺时的一些情形,大抵是爷爷感觉暮年将至,农活方面不能再像壮劳力那般拼搏,于是便决定学一门手艺,那时候农村种田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所以罗头是一件农活,以及家庭生活的好帮手,于是爷爷就找到会这个手艺的人,认真地讨教,不断地练习,最终算是摸索出了一套编萝头的思路。
俗语有云: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这话在爷爷身上,似乎从来不合适,在爷爷的内心当中,俗语不重要,学不学艺不重要,改不改行不重要,如果六七十岁的年纪,就变成一个整天无所事事,过一天是两晌,吃过饭就坐在墙边晒太阳,那么这样的日子,还不如不过。于是,不让自己歇着虚度,对他特别重要,于是便一直让自己都是忙活的状态。
如果说我的学习劲头儿还有三分的话,那么这些精神头儿,应该全部都是从爷爷那里感染而来的罢,我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是否还能有这样的精神头儿,若是有这样的身体,又是否能有一番这般心思,让自己能够放着清福舒闲不享,却要耗精费神去学一门手艺,从而让自己整日为此忙碌。
爷爷七十习得编萝头的技艺,早几年还并没有太多施展,在后来这十年间,因为承包了二爷生前留下的一片白拉条,原材料富足之后,爷爷也就开启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编萝头旅程。
上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我酷爱视频剪辑方面的技术,于是打算从爷爷编萝头的方面,来为爷爷拍一部纪录片,甚至在上学的时候在脑海里几乎排画过如何来进行拍摄,但最终也只是想想而已,不过好在,当时还算是通过手机,留下了一些视频,通过这些视频,在这篇文章里,将爷爷编萝头的日常生活,渐次展开。
# 2,白拉条。
白拉条是我们这里方言的叫法,指的就是上边图片中编成罗头成品所必须的原材料。刚才百度了一下,似乎并没有特别官方的对其的介绍,那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吧。
在我们村东南角的长沟边上,有一大片白拉条,这些白拉条是早些年二爷种的,早些年都是卖给了别人,在二爷去世之后,爷爷承接下了这片白拉条,也自此开始了一段为萝头奋斗的岁月。

白拉条一年一茬,在每年十月份进行收割,然后统一拉回家堆在一起,根部要用泥土盖着,上边再用苞谷杆盖一层,后日需用时就一点一点取出来用。也就是从十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年春三四月,这中间一直是爷爷忙碌的时光,就像上班一样的,绝不中断,纵然屋外冰天雪地,他也总在吃过饭之后,拎上一瓶茶去工作,他总说,坐着不动才冷呢,编萝头忙一会儿浑身就热起来了。

在这几年中,很多时候我可能还在上学或者在外地,父亲也在外地工作,于是多数时候都是妈妈与爷爷一起将这些白拉条一根一根割下来,再捆好,然后用摩托三轮车一车一车拉回家去。之所以强调是摩托三轮车,是因为这些刚割下来的白拉条实际上一捆是非常沉的,三轮每次只能拉那么几捆,每当割了一天之后,都要拉好几趟才能把当天割完的拉回家。
最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太同意爷爷编萝头的事情,毕竟这些时候他也已经八十左右了,这些事情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大的工程,相当耗费精神与体力,出于不忍心,因此总是阻拦爷爷,而他则不管不顾,若是没人帮忙,他则自己一个人去割,若是家里不开车拉,他则拉着架子车也会一点一点拉回家。后来见爷爷真的热爱这件事儿,又见到老爷子的确因为不停地忙碌反而使身体更加硬朗了,于是我们也都慢慢转变了态度,开始支持他的这些“爱好”。在很多我与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与爷爷一起,做了太多太多的农活了,以至于,爷爷老去的时候,母亲多次哭倒在地,她口中总说着,爷爷跟了我们没有享福啊,这么多年干了太多的活啊。但一二十年来,周围邻居都看在眼里,劝说,老汉儿跟着你们也算是享福的,开心的。爷爷,您若知道母亲在您老去之后哭成那样,应该也会不忍心就此很快地离开我们吧!

母亲和爷爷干活的效率是极高的,无论是一起去割白拉条还是之前曾经一起砍苞谷,我的速度都是赶不上他们的,一天就能割好大一片,长沟里的白拉条,四五天就能割完了。每当到下午,就很早不割了,开始扎堆捆起来,准备往家里拉。照理说捆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很复杂的事情,也的确在爷爷手里捆起来总是那么轻松简单,而我,则总是不能够轻松完成。

于是最后收尾工作的时候,一般都是妈妈还在继续割着,爷爷开始捆起来,我因为年轻身手好一些,则负责将割完放在沟坎上的抱上来,一家子人,就在这样不热不冷的天野里,尽情奋斗着。因为我抱的比较快,而又不擅长捆,因此进入了歇息状态。爷爷则一边忙活着捆,
一边言传身教地教着我如何捆白辣条,刚好有一段视频(视频拍摄于 2016 年 11 月),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在爷爷心里,他似乎是希望我能够花时间学习一下编萝头,然后传承下去的,不过爷爷知道年轻人不喜欢这些,倒也始终并没有强迫着我学什么。爷爷对上学非常推崇,经常会说起唱戏里边的芝麻官中状元之类的事儿,然而他对上学的成绩则非常包容,常常喜欢说上学这件事儿是一个分人的事儿,有的人天生是这块儿材料,有的人则天生不爱上学,是那块儿料的不需多管就能有不错的成绩,不爱上学的打着骂着也不行。刚好还有另外一段视频(视频拍摄于 2014 年 10 月),也是在白拉条地,休息间隙,又听爷爷聊起天来,,,
那片白拉条地,曾经爷爷倾注那么多的心血,记得每年爷爷还要给白拉条打药,就是怕虫子太厉害了,从而把叶子都吃光了,有几次打药,都是我去做的,上下走着非常不方便,但是依旧用心的照料着。而今,爷爷已去,没有人会编萝头,白拉条也将无人打理,再不会一年一茬那么割了,再往后它的用途,可能也就只能是用于烧锅烤火了。想起这些,总感觉伤感,爷爷的离去,几乎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他带走了太多太多东西了。
# 3,编萝头。
编萝头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单是流程就需要好多道工序,就这样爷爷每天重复着这些工作,从不间断休息,纵然工作的时间是在冬季,但他常常拿这当做热身的一件事情。
他常常在吃过饭之后,去到专门工作的一个屋子,早几年大伯家不在家的时候,就在他们家的棚下,后来这两年则在另一个伯家进行,爷爷一般会先抓一把松软的柴火,在盖上一些白拉条的干叶子,在火盆当中烤起火来,爷爷对烤火是非常喜爱的,一旦天气稍冷,则每天早上烤火是必不可少的项目,烤火是爷爷在我童年记忆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件事情了。烤了一会儿之后,感觉手上身上都热了一些了,他就开始进入工作了。
我在这里无法准确详细地记录下编萝头的整个流程,因为很多环节我也不知道所以仅能通过自己还记得的,以及视频当中记录着的,来讲述一下。
编萝头的工序还是相当复杂的,原材料的话,可能就只有白拉条,萝头细儿(萝头的那个提手),绳子这三样而已,通过整个复杂流程以及爷爷那辛勤的劳作下,就能做出结实好用的萝头来了。
编萝头的第一道工序是打底,一般爷爷会在某一晌,或者某一天专门打底,一次性打出来个十来个,然后再扔到坑里泡着,这样以来,就够接下来好几天编的了。编萝头对白拉条的运用还是很有讲究的,打底的时候,爷爷总会从白拉条堆当中拿出两捆,这个时候条上还有很多叶子,所以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把叶子给去掉,爷爷一般都是两手各抓一把,相互交叉几下,叶子就全部掉落了。
这里有幸在当时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镜头。
2015 年 12 月爷爷把白拉条从堆里拿出来:
2015 年 12 月爷爷对白拉条进行整理:
整理完了之后,就要进入捡条的阶段了,因为是打底,所以要捡稍微粗实一些,长一些,直一些的条,一个萝头的底需要多少根,都是有固定的数量,爷爷对这些数量的遵守都是非常严格的。于是捡好一个底的就用绳子扎起来,然后接着捡,一直捡的足够打底使用,才开始下一道工序。



等到捡完之后,大概就可以开始进入正式的打底了,每当做之前,爷爷都会先将整个场地认真打扫一遍,待到整个场地干干净净了之后,他才会拿出一捆捡好的条,东西南北互为交错地摆好,腰一弯,一头扎进打底的工作中去。

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操心具体流程,所以盘底需要多少根条,我也不是很清楚了,不过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到大概需要二十根左右,爷爷会先在四个方向都放好准备的条,然后先拿出两根收尾相对放在他精心挖修的一个小凹坑上,接着马上用那个固定的标尺丈量一下两边是否等长。

然后挨着刚刚的两根开始慢慢往上续,这个时候则需要用脚踩着,续够六根之后,则开始摆十字,十字对这再摆够六根,然后开始在十字的夹角处开始摆,两个夹角再各摆六根,如此围绕着中心点摆好四六二十四跟白拉条,接着再用五六根细小的条并在一起,开始在中心点上下穿绕。

就这样将小细条绕完了之后,再用一根大条将其紧紧管束住,从而更加稳定。借助于白拉条很好的柔韧性,相互借力,很快一个完整的底就被盘好了。
以上的流程,算是打底,其实这还没有结束,因为还有萝头细儿没有弄,不过这个一般都是在编萝头的时候加装上去,所以以上算是编萝头的第一个阶段。那年寒假我在家用镜头记录了下来,当时制作水平有限,只是加了一些音乐,现在原素材似乎也找不到了,因此就放出简单制作之后的吧。
刚刚在视频中听到爷爷说要把准备的条给打完,一共八个,一次性盘完八个底,其实是非常累的,爷爷也在视频中讲述了一个老话儿“艺多不养身”,这句话的出处在曾国藩家书当中,我在网上并没有看到针对这句话有什么合理的解释,而爷爷则说,艺多不养身的意思就是掌握的技能太多,事实上对自己也未必是好的,就像咱俩一样,我会编萝头,那我就在这儿忙活着,而你不会则在那儿坐着,等到中午了,咱还是吃一模一样的饭,这就是艺多不养身。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句话,而爷爷的解释又非常有意思,因此我倒是挺赞同这个注解呢。
盘一个底可能十分钟就完成了,然而接连盘七八个底,可能力气上感受还好,但在腰板儿上,恐怕年轻人没有一个能受得了,之前看书的时候,看到当年一些知青上山下乡第一次去稻田里插秧,仅仅插了半晌,腰板就疼的似乎不是自己的了,而爷爷就这样毫不停歇的忙活着,长期地劳作以及劳累,使得他的腰板儿早已经弯下去了。
下边这个视频是某一日去喊爷爷吃饭,回家的路上所拍,走在爷爷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令人心疼。
进入第二阶段编萝头,其实编萝头是很辛苦的,因为要把每一根光直的白拉条按着心中所想的样子弯折出来,无时无刻都在与白拉条进行着抗衡,年龄越来越大的爷爷,实际上手劲儿也不是特别的足了,很多时候对白拉条都只能是一种妥协的态度了。尽管如此,他从未放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
当萝头底部盘好之后,一般都会扔进水里泡着,从而避免发干,等到编的时候再取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找一个合适的细儿,卡在底的当中,然后将底整个翻上来,再用绳子围住,这样就有了一个桶状的模样了,接着就能依着这些柱子一点一点地编上去了。
爷爷的工作效率一直保持在一晌编完一个萝头的速度,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速度似乎总是不能保持了,很多时候在我去喊他吃饭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收尾。
事实上收尾工作才是整个过程最难的,因为要把最初盘底的这些条给一一捋顺,然后一一撂倒攀缠,这些条大都非常粗实,因此弄得时候相当费力,并且一个萝头编出来是否好看,这个阶段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是爷爷年龄大了,收尾阶段也往往力不从心了,从而使得萝头编出来最后的样子看上起不是那么地好看,这一点,也成为日后卖萝头的一些问题埋下伏笔。
爷爷每年从十月份开始编起,编到第二年开春,每年大概要编出两三百个萝头出来,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纯手工制作,可谓是十分辛苦。然而爷爷在做生意方面似乎并不十分擅长,他常常出于为对方考虑的角度,忘却自己编萝头的辛苦,以极低的价格将萝头卖掉。每一年爷爷都能够攒下一笔钱,大概两千到三千之间,而这些钱,则是他操心一年,辛苦半年,忙碌多时换来的,能够自给自足,想买什么不需要向儿女们伸手,这一点在他心里是非常高兴的,纵然付出与回报差比是如此地大,他仍旧非常满足于这种可以编罗头的生活。
# 4,卖萝头。
在编罗头的时候,我参与的并不是很多,而在卖萝头上,我则有那么几次与爷爷一同奋战的经历。大概集中在 2012 年到 2016 年这些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家里买了一辆摩托三轮车,在这之前,一直都是爷爷拉着架子车奔走着卖的。
下边这组图就是某一个卖萝头的日常,帮着爷爷将车子装好捆好,他便一个人迎着太阳赶往集市去卖。





关于卖萝头事实上有挺多故事的,我这里也捡几个自己印象较为深刻的点来讲述一下。
老家每年过完年都会起会,起会的时候各种马戏团杂技团都有,人也就异常的多,爷爷的萝头经常也都是趁着这些会卖出去的。家里有了三轮之后,我便经常会变成爷爷的御用司机,拉着去卖。
记得那一次是饶良起会,我与爷爷一大早就在家盘算着怎么样才能多拉一些萝头,大的套小的,一层两层装上了十好几个,然后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了一圈又一圈,因为起会的集镇距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地,所以吃过早饭我们就早早出发的,爷爷坐着一个小墩儿在车兜的一个小角落里。
大概走出有十多里地的时候,有人喊着说想买,我一看刚出门就有人想买,心里还蛮开心的,于是停下车子,过来了几个人,其中想买的是一个女人,开始她在周围转着看了看,觉得不过瘾,说能不能解下来挑一挑,做生意的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于是我与爷爷将绳子解了一半,一下子拿下来四五个,她左挑右选觉得都不满意,实际上则是为后边的砍价做铺垫。
这些萝头最早的时候爷爷卖十块钱一个,直到近几年来才要到十五块钱一个,而事实上真正以要价卖出的萝头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喜欢砍价,这个女人也是的,原本一开始说的十五,爷爷觉得是第一个开张,所以问她要十三一个,然而似乎她还非常不能满意,一再讲着萝头哪里不好,这个时候我则着实替爷爷委屈起来,因为她们不懂一个萝头编出来需要付出多少的心血,更不懂刨去成本之后,则人工费几乎是没办法计算的(因为太低了),于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上去与那女人理论起来,说你想买则买,不想买就别总说这不好那不好,卖给你本来就已经便宜两块了,而你还不知足,总觉得我们赚你多少了似的。
我说爷爷不擅长做生意,而我则是个压根就不会做生意的人,那个时候的我基本上是厌恶商人这个角色的,但却因为心里替爷爷委屈,就那样的与之理论了起来,后来爷爷在一边说着,我年纪这么大了,也不容易,这萝头买回去四五年绝对不会坏。最后他们实在也不忍心,便不再争执。然后我与爷爷再次捆好继续上路,一路上爷爷都在说,萝头也不好卖呀,她也不容易呀,爷爷永远用这样的善意损伤着自己的利益,很多时候,萝头都是低于预期价格卖出的,这成了一个常态,而爷爷则总是笑着说,他们也都不容易,妈妈每次听到爷爷这么说之后,都会说,你总是这样,别人不容易,都没有想过自己容易不,,,我们常常为爷爷贱卖萝头而心疼,但又着实地无能为力,就这样很多次重复上演着。
还有一次应该是很早的时候,李店有会,然后爷爷拉着架子车去卖箩头。李店距离我家大约二十里地的样子,并且在路上有几个非常大的坡,爷爷说这些地方都是借助于过路人的帮忙才上去的,否则仅凭爷爷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上去的。
爷爷对架子车非常有感情,可能在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还用架子车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他经常就这样毅然出发了,而且这次是带了铺盖棉被在车子上的,计划的就是晚上不回来了,在那儿待上两天。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夜晚降临,我于是就把大门给锁上了。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喊敲门,一打开,竟然看到是爷爷拉着车子回来了,我说,咦,你今儿不是不会了吗,爷,咋这会儿回来了,他说了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自己内心的震撼,敬佩与赞叹。一天之内,来回四十里,而且还拉着重重地车子,我的爷爷,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就这样风尘仆仆,从某些角度上来看,我们做家人的可能不够称职,但是老人愿意这样干,能够这样干,作为家人,除了顺着,支持,别的什么也做不了,我想,这就够了。
关于卖箩头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有很多我也都记不大清楚了,有时候经常会有人直接来到家里买箩头,爷爷也都常常便宜地卖掉了,从不舍得多问别人要一分钱,他就是这么一个质朴的老人。
现在爷爷去了,家里还保留着不少的箩头在屋子里,睹物思人,有些东西跟随爷爷而去,而有些东西,则永远在世间保留。这个编萝头的老汉儿,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并不赚钱的将箩头卖给十里八村,服务了一个又一个农人家庭,当他去世,亦有旁人惋惜,,,
# 5,其他
# 1,编鸡罩
事实上,爷爷不仅仅会用白拉条编箩头,他还会编鸡罩。
编鸡罩与箩头相比起来则要简单一些,不过也非常考验功力,每年爷爷在编萝头之余,也都会编一些鸡罩,不过并不多编,一般都是依据订单来编的,比如哪个村的谁谁捎信儿说要鸡罩了,他才会专门编一下。
鸡罩也是一样,需要先盘底:

感觉非常讲究的样子,没有两把刷子,还真是盘不出来呢。

底部盘好之后成品的样子,如下图:

编鸡罩要用上比箩头多一倍的条,而卖鸡罩的价格却只比箩头多了三分之一。

编完之后还要各种修理,以期鸡罩达到一个美观又实用的境地。
# 2,干活到废寝忘食
爷爷经常干活到废寝忘食,有时候我喊他吃饭,他则对工作恋恋不舍,不愿离去,因此有时候如果饭食比较好拿,我就直接端过去,让爷爷不用回家就能吃饭了。
看上去,好像是饺子。

# 3,干活直到大年夜
爷爷对待工作的态度,常常是我们平常人无法企及的,而这些情况在他自己那里,则基本上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如果说我个人在日常工作当中,有那么一丝丝工作狂的意味,那么这些精神的源头,则基本上也都是来源于我的爷爷,看到下边几张图片,我脑海清晰记得爷爷当时的音容笑貌,一般大年夜都是休息娱乐的,而对于爷爷来说,热闹是别人的,他只是说,下午编的这个箩头还有一点点收尾的工作没有完成,现在刚吃完饭,趁着热乎劲儿,把箩头的事情忙完,就休息啦,过年啦。

现在看着这些图片,心里满满的是温馨与动容,一个八旬老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是很没有太大价值且辛苦劳累的事情,是那么地热爱与付出,这并不是一个平常人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从很早我就体会到,爷爷身上所聚集起来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大年夜里,大家可能都在外边放炮娱乐,而我则静静地在这里陪着爷爷,听听他讲过去的事情,或者静静的与他待在一起,就非常安然,我庆幸,在后来的这几年里,我都做到了,而今年,爷爷您在腊月二十二过世,就此,再不能大年夜中,与您一起度过了。

# 4,也曾被骗过。
好多年前,爷爷在集镇上卖箩头,好像是收到了一百块钱假币,当时爷爷对此还是很伤心的,那时候我听说了这事儿,但是还小,无能为力,不过很快爷爷就看开了,不再为此事儿而烦忧了。
还有一次是爷爷在集镇上钱包被割跑了,以至于中午吃饭都没有钱,于是他就拿箩头与旁边卖饭的人换了一些饭,这是他常干的事儿,经常在集镇上用箩头与别人换一些东西。
另有一次被骗的经历,说来则十分让人愤慨了,那是七八年前了,还是爷爷在集镇上卖箩头,然后碰到了一个人说是唐河那边的,然后在这边卖豆芽,说他们需要几个箩头,不是普通的箩头,是那种非常大的箩头,要比普通的箩头大五六倍的那种,而且每个箩头出价不菲,爷爷听完之后,回来就一直把这事儿挂在心上,一边开始慢慢攒粗条,因为是特别大的箩头,所以用的白拉条自然也要非常粗的,一边思索着该如何完成这项工程,因为在这之前,爷爷从来没有编过那么大的箩头,但因为人家那样一句话的需求,爷爷就认真地放在心上了。
用了非常多的材料,费了非常大的心思,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耗了非常长的时间,最终爷爷完成了这项任务,八个如大洗澡盆般的大箩头就这么给造出来了。
然而,也不知道后来再没有那人的信儿,还是有了信儿,但不要了,总而言之,对方后来又一句话,不要了,这种特殊订单做出来的箩头,平常家庭都不会用到,因此,这八个箩头就算是砸在手里了,因为个头特别大,放在院子里格外显眼,当初做出来的骄傲都化作此时的尴尬,于是爷爷让我把他们全部都放在了大队院那个草屋里边,以期眼不见心不烦。
父亲多次针对这个事情说爷爷太冲动了,爷爷则总是皱着眉头说,那你,他不要了,你也没办法呀。后来我则多次听爷爷提起这件事儿,他说早知道当时收那人一些定金就好了,这样就算他不要了,咱也不会亏啥。我揣摩着,这事儿大概在爷爷心里,深深地伤着了。而他却又并不十分以此悲痛,继续着自己的工作,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仅仅知道这些事情,具体里边详情,有一些也并不清楚,总之那个人爽约了是事实,现在自然也不必埋怨他什么,毕竟个人业力个人负责。后来过了五六年之后,这些箩头终于没有什么去处,最后就被父亲拉出来,烧锅烤火拆掉了,依稀记得拆的时候爷爷还有很多不舍,还有很多后悔,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欺骗了他,而他,并没有做任何的嘶吼,只是静静的继续向前。
编萝头是爷爷最后这几年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在他声明最后这一年里,仍旧还有忙碌,只不过因为生病,母亲则不再让他编了,而爷爷也终于听话地歇下了,而后两月时间左右,爷爷则离开人世。现在回想着爷爷以往常说的,等老了以后,就歇着了,能干的时候,还是多做一些,然而爷爷您还未及歇息,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您这一辈子都在操劳之中,爷爷,您辛苦了。您的精神将永远保留在我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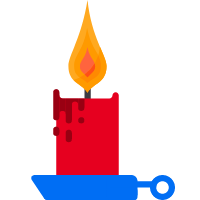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