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女的尴尬
处女的尴尬
本文写于: 2014年2月22日。
从小学到高中,我所经历的,大概语文老师是认真讲解过修辞手法的,他们讲到借代时,同大家举的例子大多是“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林觉民《与妻书》)等,然而在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闪现一个绝妙的例子:处女作(此灵感来自老师在介绍作家时的常用语),但却从来见不到老师援引此例,在自己的思想未被认同的沉默里,我不禁在心里打下一个问号:老师为什么不用这个例子?仅仅是因为当时没想到吗?
不妨假设一下,假设当时的师想到了这个例子,那么他是否会讲出来呢?不会。为什么不会?这一篇文章的探讨就从这个假定的情况开始。
我先来谈谈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是绝妙的,因为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应用非常广且频率非常高。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例子来:上学的路上我买了瓶儿饮料,进班后刚放在桌子上,要好的朋友立马就拎起来,口里并言:“你怎么知道我渴了呢?让我来破处儿。”于是我看着他把饮料的处给破了。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流行起一个风尚:班里的同学中,哪一个穿了新鞋,则大家总是要对之施以欢迎礼(朝鞋面上“盖章”,即自己的脏鞋底踩到对方的新白鞋面上),这不小五今天就穿了双新白鞋,在上课的时候已有几人挤眉点头地暗作商议,但小五似也意识到了,老师刚宣布下课,他便冲了出去,剩下这一帮争相追赶,口里并言:“让我破处…………让我破处……”。凡比种种,可谓不胜枚举,据此可见,在私下民间里,这样一个意义是被大众认可并接受的。因此,综合考虑,我说这个词儿作借代的例子是绝妙的。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便可以看到“处女”的应用(处女地,处女作),遍看文学作品,则对这一个意义的应用更多。为什么我们写起来就很“顺理成章,理所正当”,在说起来就很不舒服,很尴尬呢? 这一个独属于“处女”的尴尬该怎么解释呢?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男女等,甚至女权泛烂的时代。那么从某种角度上考虑,“处女”这个词儿所表达的意思似乎并不严谨,因为这个词儿的存在更加强调了一些腐朽的性观念,因而在封建固守的情形之下,没有老师会在讲借代的时候用“处女”作援例。
至于如此苛刻吗?
诚然的,文化能塑就观念,我们常常似也乐于顺应这观念。但是,反过来看,为何观念就不能包容文化一些呢?显而易见,我们的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会有波折,会有磨难,但总是会走的,走向更真理的那一层。
到那一个时候,老师讲课引例“处女”而无尴尬,学生回答时亦无尴尬,因为真诚的文化应该能够开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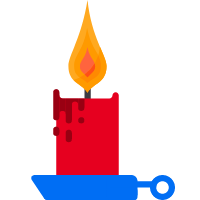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