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那年俺家的一套三(父亲所作)
难忘那年俺家的一套三(父亲所作)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又到了一年一度秋收冬种的季节。
2020 年对于全球的人们来说,可谓是命运多舛大灾大难的一年,然而在家乡那片广袤的黄土地上,却默默地给人们带来了惊喜与期待,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此时此刻用"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来歌唱最合适不过了。
随着大型农机具的推广使用,秋收的步伐在现代化机械的隆隆声中被强势推进,短短几天时间被各种农作物覆盖的黄土地便露出了它原来的面貌,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但等秋分节气一到,中原大地便拉开了冬耕种麦的序幕。
此情此景不由地勾起了一段尘封在我记忆中不堪回首也难以忘怀的陈年旧事,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在家乡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亦步亦趋举步维艰的一套三,它就象定格在我生命里的一副精美图画,让人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生产队解散的那一年,我们家分得了一头驴,就象驴的"嫁妆"一样,随驴分得的还有一盘石磨、面柜子、粗箩细箩各一个,因为这些驴的家伙什分给别人家也没有用,其实这些逆潮流而生的东西分到谁家也用不上了,只不过是给它找个合理的归宿罢了。
自从我家分得了一头驴,分到牛的人家便小声地议论着,你一嘴我一嘴,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穷人家吧,偏偏分头驴,这犁地种麦的事呀我看够呛"。也有人俏皮地说:"如果靠吼(指驴叫)能犁地种麦的话,他家绝对是第一”。更有人调侃着说:"走里快了撵上穷,走里慢了穷撵上,不紧不慢走几步吧,噗噗通一声又掉进了穷人坑,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他家的穷命运就象他们分的那头老驴拉磨一样,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圈″。

随着生产队的解体,驴拉磨的故事也告一段落,分到我家的驴也从繁忙的磨面事业中解脱出来了,于是吃饱没事干的时候便来了精神,驴叫不改的本性又显现了出来,时不时地练练声,嗯啊嗯啊地来那么两嗓子,那高亢浑厚的吼声顿时响彻大地,晃晃悠悠地飘荡在小村上空,似乎是想用它豪迈的歌声来刷存在感,并以此来向人们发泄心中的不满,谁说俺老驴拉磨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圈,在气质这一块俺还是拿捏的死死的,不信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要说驴的叫声在牲畜界没有能出其右者,不管是哞哞叫的老黄牛,亦或是嘶声短暂的高头大马,都无法与之抗衡。骡子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压根就没有听它叫过,也许是因为它既没有可以炫耀的祖先,也没有可以传宗接代的子孙,一直处于自卑状态中不愿发声吧。
看着墁上拴着嗯昂嗯昂乱叫的犟驴,父亲一时间愁眉莫展,无计可施。看看离犁地种麦还有些时日,父亲也不和家人商量便支张着盖了一间草房,并脑洞大开地支上了石磨,又请来锻磨匠锻凿了磨盘,想让闲着乱叫的驴重操旧业继续磨面事业,大有"反清复明"之势,孰不知驴拉磨的历史气数已尽,终因现代化磨面机的普及而无人问津。就象《黔之驴》中的驴运到贵州,至则无可用而被放之山上。父亲异想天开想让驴拉磨延续下去的故事也就无疾而终、嘎然而止了,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在滚滚红尘中。此举后来这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笑资。

说话间到了秋收大忙季节,清闲一时的驴此时总算派上了用场,你别说忠厚可爱憨直倔强的驴确实有一股犟劲,一但接到指令,一架子车重达千斤的农作物在松软的土地上被它纵着身子拼命地往地头拉,虽然力量有限却非常舍得卖力气,尽管人们叫它笨驴、蠢驴,但它却能忍辱负重、从不计较,在秋收拉庄稼这方面确实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
一晃,秋收接近了尾声,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早早地合计着种麦的事,分到牛的人家都"门当户对、势均力敌"的找到了搁犋(包产到户刚使行单干时,农家大多贫苦,牲畜欠缺,农具不全,无法独立完成耕种,需要两家或几家合伙,也叫搁犋)伙计,唯独我家那头高傲的老叫驴孤零零地拴在墁上嗯昂嗯昂地叫着,试图想以它美丽的歌声来吸引邻居们的注意,然而人们对它的举动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这也怪不得别人,因为人家分的都是能犁地耕田的老监子(阉割过的公牛)或者是身材健壮的母牛,实力搁哪儿摆着呢,而我家分的却是个头不算太大的一头驴,我们岗上的黄士地土质比较硬,犁起来比较费力,显然驴和牛比起来差距一目了然,谁也不愿意与我家示好搁犋。万般无耐之下父亲厚着脸皮央求老张家与我家搁犋,由于老张与我哥是一担挑(连襟),碍于亲戚关系磨不开脸面只好勉强同意。

大家都知道驴拉磨、拉辗、拉车都是它的强项,而对于犁地来说完全是角色错位,就象小品《策划》中能下蛋的公鸡一样,不是它的活硬要让它干,实在是有点免为其难。我们也只能称赞它为驴中楷模,牲畜界的战斗驴。
战斗首先在老张家的责任田里打响。因为老张家分的是生产队里久经沙场、能征善战、身材健壮的母牛,我们象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就谦让着让他家先开犁。
牛驴搭档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号令不统一,牛右转是哒哒、哒哒,左转是喔喔、喔喔,而驴的右转恰巧是喔喔、喔喔,左转是依依、依依,这样牛的左转和驴的右转就产生了矛盾,由于套熟的母牛当墒(指有犁地经验的牛走外边也就是右边,起到领路的作用)是主角,重新上岗业务不熟的驴是配角,犁到地头需要左转时当然以牛的号令为主,牛自然而然地左转往里拐弯,而任性倔强的驴听到"喔喔″的口令刚要右转时,却被体积数倍于自己的老牛不情愿地扛了回来,心情郁闷的驴心里想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工作,怎么突然间连号令也改变了方向,真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实在是丈二和尚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走错方向不仅要挨骂甚至会挨鞭子的,驴心里盘算着反正挨打也不是我一个,怨就怨你这老牛惹的祸,战战兢兢的驴见不仅没有挨打,而且也没有挨骂,时间一长,驴也逐渐转变了心态并接受了现实。
尽管驴非常卖力,拼命工作,但犁地这个活实在不是它的长项,大炮杆(挂在犁子前边一种耕地的工具)牛这一头始终占据上风,就算它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与牛持平,异常吃力的驴走起路来一摇三晃、步履蹒跚,无可奈何只好到这头喘口气,到那头歇一会,犁地整地的速度明显落后于那些"门当户对"的邻居们。
当别人家都犁完种完,稍早一点的麦子甚至都出来了,空旷的田野上依然传来父亲驱使牲口耙地的声音:"哈,怼球!扛吧,你鳖子你"实力悬殊左冲右撞的驴总是免不了父亲的责骂。
生产队解散实行单干的第一年,我家的小麦一直种到小雪节气,农村有句俗语"小雪不露土,大雪不分股"。当别人家的小麦"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时候,我家的小麦却如同"盖着盖头羞涩的新娘”迟迟地不肯露出庐山真面目。事后老张感慨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们恐怕是连公粮也交不起呀"!父亲听出了弦外之音,知道是我们拖了人家的后腿,满怀歉意地拍着胸脯说:"放心吧,明年种麦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我早想好了对策,你就等着瞧好吧″。
为了兑现给老张许下的承诺,在邻近各乡镇当时风靡一时的牛绳上(交易牲口的场所)不时地出现父亲准备买牛的身影。当时的行情是能使的母牛贵的惊人,就连几个月大的母牛娃也动则上千。囊中羞涩的父亲眼光只好瞄准牤牛娃,然而稍微能看上眼的牤牛也要五六百。在万般无耐情急之下,父亲只好又牵回了一头相对比较便宜的老叫驴,人穷志短,没钱你就无法任性,在那个拿鸡蛋换盐吃的年代,我无法想象我家哪来的买驴钱,因为我读初中第一学期的学杂费十三块六也是在班主任多次催促下,至到期未方才补齐,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艰苦岁月中的辛酸场面,你就不知道生活有多严肃!人生有多无耐!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父亲居然忘记了"一个槽上拴不下俩叫驴的常识"。两头生性好斗的公驴见面就象仇人一样分外眼红,互不相让又踢又咬,无耐喂的时候只好在牛槽旁一头拴一个,让它们井水犯不着河水。
我们岗上的地单凭两头驴是无法完成耕种任务的,第二年犁地种麦的时候依然是和老张家搁犋。就这样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套三就应运而生了,具体操作方式是在大炮杆的一头又挂上一个大炮杆,两个大炮杆刚好多出一个牲口的站位,两头实力弱的驴共用一个大炮杆,以二合一的力量对抗老张家的母牛,不管咋说这招还真灵,三头牲口相比于那些"势均力敌″的邻居们并不逊色,种麦的节奏总算没有落后,老张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父亲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麦子一种完,两头拴在墁上闲下来的叫驴便开始热闹起来,它们就像参加青歌赛一样互飚高音;有时候又象对山歌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时候却又更象是二重唱,这边还没唱完那边就接上了,唯恐在气势上输给对方,那刺耳的嗯昂嗯昂声震耳欲聋,大有余音饶梁、三日不绝之气势,绝对称得上过去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也给平常寂静的小村增忝了一些生活气息。
一套三虽然解决了犁地种麦的问题,但接下来的事却比较棘手。一是两头老叫驴喂起来比较麻烦,二是它们已经没有了利润的发展空间,对于我家当时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来说,在长达一年的饲养过程中没有利润可寻是不现实的,于是父亲果断地处理了后来买入的那头叫驴。

农闲时节,在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牛绳上,又出现了父亲准备买牛的身影,其实去之前早已盘算好了,准备买一头“杆长蹄正身段好”有发展前途喂到明年种麦基本能使的牤牛,凭着“拱腰驴,凹腰马,弯弯腿牛不用打”的口决,经过仔细审查认真挑选,最后在牛经纪清脆而响亮的行鞭声中(牛经纪手中的鞭,鞭杆短鞭身长,就象过去皇帝上早朝太监在朝堂门外甩的鞭子差不多,一般人还真甩不响,鞭声一响就意味着生意成交,不能反悔,有点雷同于现在拍卖行中主持人手中的锤,一锤定音的意思)以五百元的价格买下一头半大不小的牤牛娃,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其中有我二伯"帮牛腿”的钱。
“帮牛腿”是八十年代初生产生队解散后,实行包产到户单干时,种地困难的人家互帮互助的一种耕种方式。一些买不起牛又没有饲养条件的种地户会主动找有牛的人家兑钱或兑物帮助种地。"帮牛腿″是那个特殊年代产生的新名词,随着时代的发展,岁月的变迁,如今它就象一粒尘埃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宇宙中。

既然说到了"帮牛腿",就不由地想多说两句和我二伯之间关于帮牛腿的故事。我二伯打一辈子光棍,跟我奶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单身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他性情孤僻,脾气暴躁,不但鲁莽甚至有点自私,父亲常说他有点“楼”。记得小时候生产队里分给他的几竿湿粉条挂在墁上凉晒,让我帮他看着不让满地乱跑的鸡子吃,贪玩的我一不留神被鸡子叨吃了掉在地上的碎粉条,暴跳如雷的二伯便满庄撵着打我,吓得六神无主的我急忙跑回家,到母亲跟前以为有了庇护,但还是被他打了一顿方才解气,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我二伯"帮牛腿″是讲好了只兑钱,不参加饲养,也不参与养牛产生利润的分红。虽然他只兑了少部分"帮牛腿″的钱,但犁地时必须先给他犁,稍不如意就讨要"帮牛腿″的钱,再不然就拿刀吵着要砍牛腿。就跟小孩们在一起玩耍一样,出现矛盾和分歧时,就翻脸说:"你昨天还吃俺家一块馍里,还给俺"。看热闹的邻居们都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父亲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什么事情都让着他,免得触动他那根发疯的神经。
到第三年种麦之前,经过父亲近一年的精心饲养,这牤牛还真气,居然长得出奇的快,不仅骠肥体壮,而且身材魁梧,邻居们都说老李今年犁地种麦可是不用犯愁了。父亲更是早早的让它学活,拉着一块三角形的捞巴石(过去打场挂在石滚后面的石头)满庄跑,并教它一些基本的哒哒咧咧左转右转之类的用语。然而此牤牛却有一缺点,就是除了父亲眼里容不下别人(抵人),拴在墁上的树上没人敢解它的牛绳,就连生人从它身旁路过它也横眉瞪眼,前踢不停地扒着地,鼻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一副盛气凌人桀骜不驯的架势。

真到犁地的时候,一切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依然是和老张家搁犋,由于它桀骜不驯的性格,刚开始父亲只好在前面拉着它一起走,毕竟是牛娃没有长劲,个子不小却途有其表,犁几遭地就开始耍赖,牵着不走打着后退,老张说这可咋整,这也不是个办法呀,父亲微微一笑说咱不是还有驴吗,留一头驴就是为了防备这种情况的,说话间便回家牵来了驴,依然釆取一套三的模式,老张家的母牛仍然当墒走右边,牤牛和驴共用一个大炮杆,驴走中间,牤牛走左边,刚开始就象天鹅、梭子鱼、和虾拉车一样,劲使不到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倒也勉强凑合,慢慢的才逐步走上正规,与上次的一套三比起来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要有人牵着走才行。
过去犁地需要一个人专门擓着筐子或萝头在前面撒化肥,轮到我家犁地的时候,这一任务主要由我来完成。而套不熟的一套三又必须有人牵着做向导,为了节省人力,渐渐失去锋芒的牤牛便由我牵着边撒化肥边在前面远远地领着,生怕被它抵着,毕竟一看到它横眉瞪眼的架势就有点提心吊胆,步步惊心。
牛有反刍的习惯,有经验的牛把式犁到半响都会停下休息一会,让它们倒倒沫消化消化草料,牤牛娃子歇一会就不老实开始犯贱,它一犯贱不打紧,牛套驴套就乱成了一团麻,那情景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若与两头套熟的牛比起来其中的麻烦程度让你简直无法想象也体会不到。
生产队里一路走来的牛,不管是老犍子或者母牛一般都比较老实,中间休息时即使跳蹄(牛腿站在牛套绳外面)了,只需用鞭杆按住套绳对它说:"蹄、蹄",它便知道把腿抬起来站在套绳里面,既省时省力又省事。而对于初出茅庐刚入江湖的牤牛来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老虎拉车根本不听你那一套,稍不留神还有踢着你的危险,无可奈何只好重新套过,就这样我们家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又艰难地度过了一个种麦季。
当年一套三的壮举也并非我们一家独创,邻近村庄也有不少,它虽算不上劳动人民的智慧,但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劳苦大众被逼无耐、大胆尝试的一种耕种方式。
在我的记忆中,一套三的耕种模式好像仅仅持续了两年就被父亲否定了。父亲是在别人家一阵阵的鞭炮声中被惊醒的,过去我们农村有一个习俗,谁家母牛要是产一牛娃,三天之后要放一挂鞭炮以示庆贺,产的要是母牛娃那更是喜不自尽,养一年下来能卖千把块钱呢,在当时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对于一个急需经济发展的贫困家庭来说,只考虑犁地种麦是远远不够的,你还要考虑经济效益,一头公驴和一头牤牛显然不能产生这样的经济效果,人们常说:"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你就穷″。
图片
于是过罢年,牛绳一开市,父亲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以八百元的价格卖了抵人的牤牛,实际到手七百八十元,其中二十元是牛经纪的管理费(当时也叫横头),一头接近成年的公牛喂一年净利润二百八十元,若是同样大小的母牛价格可能会翻一翻。卖完牤牛接着便处理了老叫驴,为什么说处理而不说卖,因为一百九十元的价格实在算不上卖,要搁现在这点钱恐怕连一张能做阿胶的驴皮也买不到。
卖完公牛和叫驴,家里又七拼八揍地终于买了一头将近能使的母牛。当父亲还沉浸在一年下一个牛娃,三天也可以放鞭炮的喜悦之中时,那些生产队解散时就"门当户对″的邻居们早已积攒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悄无声息地把手扶拖拉机开回了家,更有甚者开回了四轮拖拉机,父亲看着这些洋玩意不无感慨地说:"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一步撵不上,步步撵不上啊"!
小时候我总认为日子会很长很长,长大后才知道人都会慢慢变老,岁月似乎是在慌慌张张之中偷走了父辈们的人生,如今把我们拉扯大的那一代老庄稼金、牛把式的父辈们大都已离我们而去,静静地长眠在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家乡的厚土。而那些被他们使用过的并不遥远的牲口用语"哒哒咧咧喔喔依依″,以及那个年代"帮牛腿″的故事,也只能成为六零七零八零后的一种记忆,九零后以后的年轻人将不知所云,包括现在的牛马驴骡也一定会当成耳旁风,感到莫名其妙。随着日月的更替岁月的流失,将来的人们也只能从教课书上知道驴拉磨牛耕田的故事,那犹如昙花一现的一套三很有可能被他们认为是天方夜谈,不可思议。
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农业机械化也逐步深入到了千家万户,老家的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种地已不再是农民的唯一选择,牛马驴骡也不再是劳动生产的主力军,人们不再为犁地拉车而养牛养马,不再为拉磨拉辗而养驴养骡,它们好象完成了历史使命似的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昔日墁上牛马成群的现象也逐渐消失了,整个村庄甚至连一头牲口都很难找到,变得空荡荡静悄悄的,再也听不到驴吼马叫的声音,更看不到地里牛拉车犁地的身影。古老的村庄唯一不变的是世代流传下来的乡音和方言,千古不变的民风与习俗,邻里乡亲的亲情韵味,还有那静静地陪伴在小村四周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梦想的黄土地。
忘不了那些年走过的青葱岁月,也忘不了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苦涩记忆,更忘不了父辈们一路走来历尽艰辛的样子。历经了多少载的花开花落,也度过了无数个的阴晴圆缺,慢慢的学会了看淡世上的悲欢离合。如今回忆过往,那一幕幕刻在生命里的记忆总能给我疲惫的生活里注入前行的力量!
迎着初冬一轮惨淡的朝阳,薄薄的晨雾无声无息地弥漫在小村四周,此时此刻我站在家乡熟悉的田埂上,回首以往,思绪万千,泪湿眼底。

在迷迷茫茫的晨雾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不远处当年父亲犁地时那熟悉的背影,步履蹒跚的一套三也正慢慢的、慢慢的向远处走去,也隐约听见了父亲驱赶牲口的"哒哒咧咧″声,那声音不仅饱含着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大声呐喊,也似乎是在诉说着属于他们那个年代寂寞无耐而又伤心的的歌。
沧海桑田,世事多变,如今我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擓着筐子撒肥的少年,再次触碰那些埋藏在心底的思念,难以释怀的依然是那些和父辈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后注:此文首发在《乡土中原》 (opens new window)公众号,同步在此,时常拜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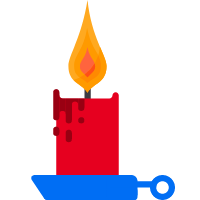
 |
|